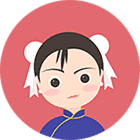
李**
Lv.2 二星
2020/01/08 10:20
李贽
万历十五年,四海升平,无事可记。有位文官叫李贽,丧妻后准备割舍尘世负担,追逐自由。于是次年剃发为僧,那年他61岁。李贽喜欢听书,藏书很多。我认为他是一位很会自我营销的人,知识贩卖。结交的都是上层文官圈子,这样可保自己衣食无忧,同时还能听书写书,刊印成册如《藏书》《焚书》《观音问》。就这之后的14年间,他和好友耿定向,耿定理的辩论,都透露着深刻内心的矛盾。他崇尚自由,却又赞成伦理道德的禁锢;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却安然接受来自道德的馈赠;他提倡实践,而成为理论家。所以作者说他像15世纪意大利的哲学家马基雅弗利---特别鼓励政 治家在需要权宜之举从事邪恶。李贽的“舍小节而顾大局”理论,体现在他对张居正、戚继光、俞大猷的肯定和推崇,纵然在张居正被清算之后。在当时来说,也是超级敢讲之人。由于李贽一直活跃在文官上层,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的观点与当时的伦理道德格格不入。最终在70多岁时,遭到了张问达的参劾,内容无非就是生活作风问题。最终自刎于狱中,在75岁那年。李贽活得太长,所以导致了他晚年身败。可如果他如其他的无名思想家一样飞鸟过境了无痕,我们又怎会知道那时的文人内心的挣扎和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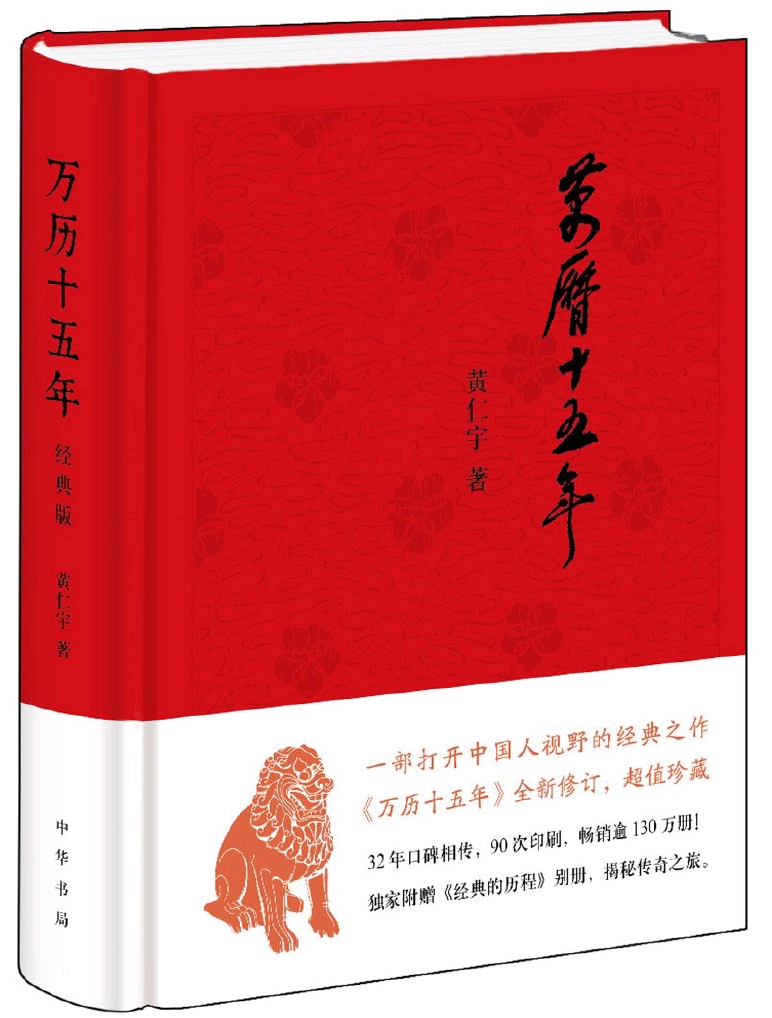
领书计划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