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
Lv.3 三星
2022/05/16 21:30
永恒的诗人
像你这样,生来就要展示,永恒的悲剧诗人,你必须在反掌之间把毛细血管转化为最可信的手势、最实在的物品。于是你开始了作品中史无前例的暴行,在可见中寻找内心所见的等价物,越来越急躁,越来越绝望。那是一只兔子,一间阁楼,一个大厅,里面有人走来走去:那是隔壁一只玻璃杯的声响,窗前的大火,那是太阳。那是教堂,山谷中教堂般的石崖。但不够;最后塔楼也得进来,还有整列的山脉;还有埋葬风景的雪崩淹没了舞台,为了不可捉摸之事而堆满实物的舞台已不堪重负。此时你无法继续了,你折在一起的两端彼此弹开;你疯狂的力量源于有弹性的棍棒,你的作品什么也不是。否则谁又能理解,你临终前不愿离开窗前,如你一贯的固执。你要看路人;因为你想到,倘若某一天决定开始,是否也能让他们变成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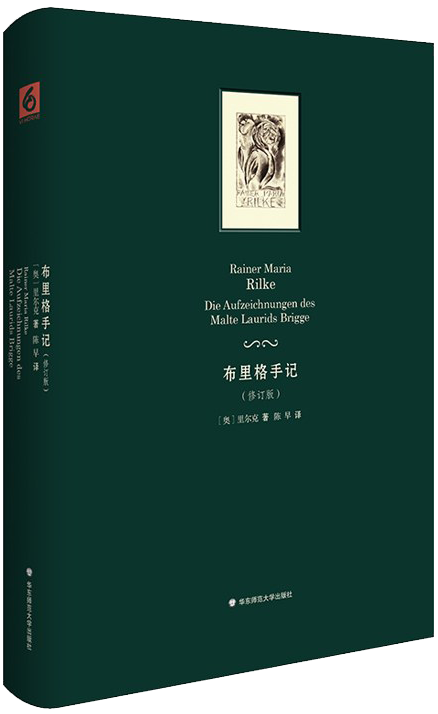
领书计划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