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
Lv.1 一星
2022/07/29 08:52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分享内容:茨威格和当时年轻人一样,在1924-1933年那难得的十年光景里,迫不及待地在欧洲大地上四处旅行。他作为畅销著作的作者,经常往来于意大利、法国、德语国家参加演讲和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这其中有一次旅行令他既紧张又兴奋,那便是1928年的夏天远赴圣彼得堡去参加列夫·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在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作者因为苏俄方面展现出来的蒸蒸日上但又表里不一的状态,时而感到赞叹不已,时而又感到唏嘘不已。他带着敏感紧张的神经,以旁观者的姿态在苏俄小心翼翼的度过了两个礼拜。除了欢欣鼓舞、热情自信的苏联人民,带给作者心灵撞击的还有托尔斯泰那座沉默不言的无名墓地。 茨威格把自己带到苏联的物件以互赠的方式留给了当地的朋友们,回程仅剩下空空的行囊。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两年后,作者再次到访位于意大利索伦托的高尔基的疗养地,在那里他见到了一个朴实自然的驼背老头,也见到了年轻人对其十分不敬重的样子,而高尔基则把在索伦托的疗养生活称之为流亡。在萨尔茨堡,茨威格因为私人事情给墨索里尼本人写了一封信,以请求帮助,结果得到了正面回应。在感到意外之余,作者也为此收获了一份文学创作之外的成就感。同时,这座位于奥地利边陲的小镇萨尔茨堡,也因为音乐和戏剧而成为了享誉欧洲的艺术之都。各种类型的艺术节把来自不同国家的优秀作品和艺术家吸引到此,在1924-1933年的这十年间,萨尔茨堡成为了欧洲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朝觐圣地,作者在当地的住所也成了国际会客厅。在喧嚣之余,茨威格坚持从事著名人物手稿的收集工作,他在十五岁读中学时,就有这种业余爱好,到如今这项爱好已经发展成为一项独门绝技。特别是在茨威格把收藏名家手稿的标准拔高(由数量转向质量)以后,他逐渐成为了这个行业里的权威。在那些他最得意的收藏中,有达·芬奇的工作笔记、拿破仑的军令、巴尔扎克的小说、尼采《悲剧的诞生》的手稿、歌德《浮士德》的手稿,以及众多音乐家如巴赫、莫扎特、肖邦、勃拉姆斯、舒伯特的乐谱手稿,甚至藏有贝多芬的临终遗像素描。1931年11月,作者迎来了五十岁生日。没有职务和职业羁绊的他以读书、写作、旅行、收藏等这些他感兴趣的方式走过了半百人生。过去也曾经历一战磨难的茨威格,在庆生当天与友人感慨岁月之时,也不曾预料自己的著作会被禁止、销毁,没有想到今后不得不背井离乡、浪迹天涯,不会想过已经稳固自得的生活有一天竟会分崩离析。在本章最后两三段的文字中,作者难以隐藏地流露出心力交瘁的厌世情绪,并且还悲观的预感到自己的人生将会被一股无法抵挡的横流连根拔起、彻底击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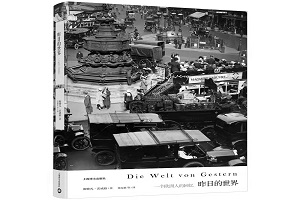
领书计划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