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
Lv.0
2022/08/06 10:28
第三天
相比困顿的物质环境,新亚早年的教授,堪称明星阵容。钱穆和唐君毅不用说了,另外还有吴俊升,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是杜威的学生。教经济的张丕介、杨汝梅,早就誉满大陆。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教西洋史。孙中山儿子孙科的秘书梁寒操教写作。诗人、书法家曾克耑(端),历史学家左舜生,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国学家饶宗颐、罗香林等等先生,都曾经在新亚任教或者讲学。上世纪50年代初,全香港只有一所学校有资格称为大学,就是香港大学。新亚书院被叫做“野鸡大学”,门口挂了一个“新亚书院大学部”的牌匾。有一天,香港教育司司长高诗雅来巡视,看到这个招牌也笑了,虽然教授名册让人刮目相看,但是碍于港英政府规定,高诗雅还是叮嘱,把牌匾取下来,别公开挂在外面。1952年7月,新亚书院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余英时和张德民两位毕业生参加了仪式。钱穆因为身在台湾,没能出席。不久后传来消息,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讲学时被天花板砸伤,击中头部压至重伤,在台湾养病长达三个月。又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钱穆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他,内心真为他难受。很多年以后,钱穆去世,余英时写了一篇文章悼念老师,他在文章里回忆那天的场景:“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叶老告诉我一个细节,钱穆先生曾经谈起他心目中的“新亚精神”,他说:“没有理想的吃苦,那是自讨苦吃,有理想的吃苦,才是一种精神”。1954年是钱穆的六十岁寿辰,但他仍然为了新亚书院的前途,在港台两地奔波,换钱来补贴学校的日常运作。他是一个极其勤奋的人,但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学术年谱,就会发现,60岁时的钱穆没有作品出版,61岁出版的也不过是在台湾的演讲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此外,正式的论文只有《孔子与春秋》,还有一些给《新亚校刊》等杂志写的零零碎碎的文章。可以说,这个阶段,是钱穆学术的低谷期。现在人看钱穆,一般认为他的主要成就在1949年之前,还有1967年去台湾以后。他的两部代表作《国史大纲》和《朱子新学案》,分别在这两个时期完成。对于1949年到1965年,钱穆旅居香港办学的这16年,因为没有重要学术著作问世,大家一般都是选择性忽略,提的并不多。但实际上,新亚书院是钱穆人生中的重要一页,寄托了他全部的文化理想。钱穆88岁高龄的时候,眼睛已经失明,在由他口述、太太胡美琦记录的自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里,他静静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师友杂忆”部分一共20个章节,仅“新亚书院”就占了五章,达到四分之一之多。钱穆在书中,这样说:“自创校以来,前后十五年,连此前的亚洲文商学院夜校一年,一共十六年。是我生平最忙碌的十六年。”的确,这16年,钱穆的主要精力并不在学术研究上,而是在为新亚书院的前途奔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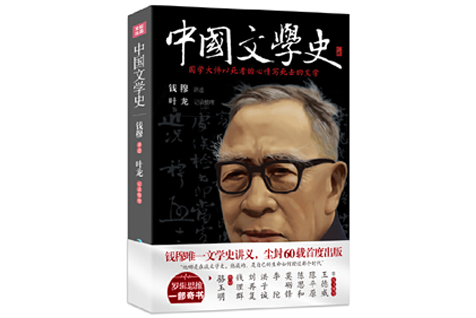
领书计划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