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
Lv.0
2022/08/08 00:50
第四天
这种在绝望中建设的大勇气,始终贯穿在钱穆的讲稿里。例如,他明白“旧文学已死”,却始终不放弃,呼唤包容,呼唤共存。他说文学家各有各的长处,没有人是十项全能;文体各有各的价值,谁也不能一统天下。司马迁精于写史论而不精于诗,跟他同时代的胡适并不能作诗,胡适的“八不主义”也只是一种议论;他还说:“现在生物已经进化到人类,但其他动植物仍然不能不要。所以有了白话文,仍然可以存在其他文体,不能单用白话文学史,来代表全部过去的历史。”他批评“红学”崛起,质疑那些沉浸于“儿女亭榭”的人们,难道要以“红学”济世?他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有巨大影响,并不是提供了一套理论,还是有一套新文学帮助。对于那些抨击他的新文学阵营,他平心而论,“通俗文学有力量,但这种文体,并不能用来讨论严肃的文化思想”。他对魏晋南北朝十分偏爱,对建安文学更是不吝笔墨,不仅把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而且对它的评价与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我想,也许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的中衰期,从政制和人格上都是黑暗时期,和钱穆前半生经历的动荡时代太相似。时代转型中,钱穆一直怀抱忧患意识,思考中国文学的未来。在他看来,中国从来没有“纯文学”的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学,是和人生、历史、天地高度融合的,所以他说:“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死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在他看来,一切通俗文学最终通达于上层才有意义,“像乐府、传奇、词曲、剧本、章回小说,都是愈往后,愈繁盛。”所以他很怀疑,新文学如果只限于神怪、武侠、恋爱、侦探等游戏消遣,会不会逐渐没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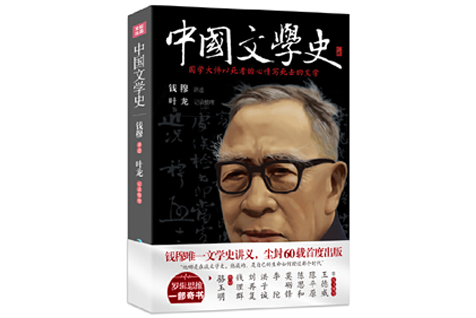
领书计划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