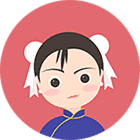领**
Lv.0
2022/08/08 15:24
第五天
钱穆先生的这本文学史,我读了很多遍。最大的感受是,他终究还是个历史学家。他有浓重的儒家情结,非常看重个人入世,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对现实主义的文学家,评价都特别高。举个很小的例子,李杜齐名,但钱穆认为,杜甫在李白之上,为什么呢?他的原话是:“杜甫如一片枯叶,任由狂风吹飘。他是在大时代中无足轻重的一粒沙、一片叶,但杜诗变成了史诗,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整个的时代。”在他看来,文学必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所以他认为杜甫高于李白,陶渊明高于谢灵运,韩愈是唐代古文的第一人,屈原和司马迁是古往今来两个最伟大的文学家。怎么说呢?也许很多人不赞同,会觉得钱穆先生的评价失于偏颇。但我们换个角度来想,他对这些文学家的评价,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和投射呢?就像他说的,“杜甫是大时代中无足轻重的一粒沙,但杜诗变成了史诗,杜甫的全部人格与时代打成一片,和历史发生了大关系。”每个人只有对自己的知音才能同气相求,这本文学史里所有的价值排序,在我看来,都是钱穆从历史里找到的精神坐标,也是他用来和自己所处的外在环境相对抗的一种“武器”。想想看,为什么钱穆会在1949年以后,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传统文化坚定的领导者?他的偏颇和偏执,你可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坚守。为什么流行歌曲会唱“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为什么直到今天,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大家族,会比我们这些在国内生活的中国人更重视乡音、乡情,更保守,也更传统?因为他们再不坚守,就连自己的“根”都没有了。所以读这本书,我自己读到更多的,其实是一种精气神,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某个特定时代的内心世界。陈寅恪先生说过,对古人要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苛求是不正确的。所以这本书出版以后,争议特别多,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说钱穆先生对西学偏执无知,而且厚古薄今,包括他对文学家的各种判断,都有很多人不认同。但我始终觉得,这些苛求都是技术性的,并没有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真正理解这本书。如果我们把它还原到1955年那一间破烂不堪的教室,面对白天去搬砖晚上来听课、传统文化成为他们最后的“根”和“家园”的普罗大众,钱穆只能,也必须讲出这样的《中国文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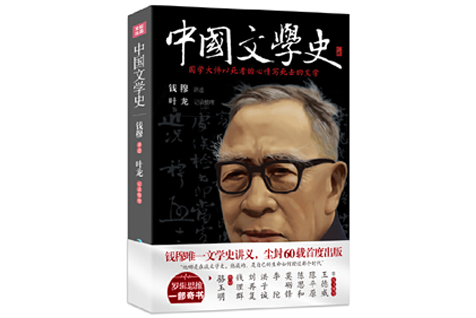
领书计划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