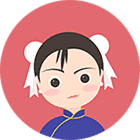领**
Lv.0
2022/08/09 08:55
第五天
2016年,这本书在上海新华书店做新书首发式的时候,我特别尊敬的一位老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老师来到现场,我当时问了骆老师一个问题:“中国文学史,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有什么价值?”它不像金融啊,法律啊,外语啊,学了就能用,就能变成钱,甚至,在大学中文系的课程里,它连文案写作这样的课都比不上,因为“没有用”,对我们的生存没有直接的用处。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文学史呢?我记得骆老师当时的回答是,中国文学史就像我们中国人的“乡愁”,没有它,你可能连自己的出处都找不到,而人是不可能只吃饭、没有精神家园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钱穆版文学史面世之后,引发了一场长达5个月的关于文学史该怎么写的系列访谈,有将近30位学者,或者接受采访,或者自己写文章,几乎每个人,都在文章里激烈地捍卫自己的文学史观。我记得,刘再复老师在访谈里,略带嘲讽地说,当代文学史重写了那么多年,至今还是个“梦想”,也许永远不会实现。从上世纪80年代激进的理想主义走到现在,青丝变白发,学者们越来越明白,文学史的重写和共和国历史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谈何容易啊?现实主义者选择了远离,再也不写了;理想主义者仍然在修改自己的文学史,不管能不能出版,像陈思和老师;更多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斡旋,或者转向考据,或者出走海外,或者和钱穆先生当年一样,走入民间,下社区、进企业,但凡能做点普及工作,从不挑拣。通过那次访谈,我深刻地意识到,学术有的时候,真的不只是一碗饭。当知识分子无法选择,他们的研究就会成为他们最后的精神堡垒。看懂了这些,再回头看钱穆和他的这本课堂讲义,就能真正做到“同情之理解”。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曾经很想在里面找到钱穆先生内心世界的蛛丝马迹,后来发现很难,钱先生是那种典型的中国文人,内敛、婉约、感情很少外露。但还是有一处,让我读到很感动。他当时讲到屈原的《离骚》,非常难得地对台下的年轻人说了一句题外话。他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不求人解,就像屈原写《离骚》,这个社会不用他,他有怨,也有不甘心,但他怨得纯真而自然——如同行云流水,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我们的人生遇到悲欢离合的时候,也当如此。回头一想,“不求人解”这句话,或许也是钱穆对自己的勉励。他一生守护中国传统文化,不曾言悔,只在极偶然的间隙,才留下对时代变革的一声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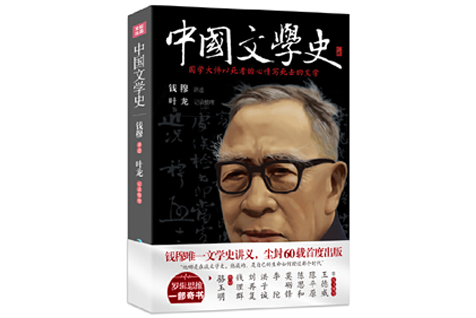
领书计划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