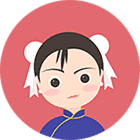领**
Lv.0
2022/08/12 08:35
第九天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钱穆的考据功力,他在书中根据诸子百家的文章体例,认为《墨子》出于《论语》之后,而在《孟子》之前,因为它既有《论语》任意命名章节的痕迹,也有《孟子》严整归类的痕迹。他在讲述《楚辞》时,认为屈原所描述的是襄阳与南阳,在湖北而非湖南,所以洞庭湖与湘江都在湖北,“湘”即为“相”,“湘流”实为“汉水”,“洞庭”实为“此水通彼水”之湖,因此它并非特指,而是统称。司马迁认为屈原《渔父》中所说“湘流”在湖南,与屈原在湖北自沉相矛盾,因此改成“常流”,实际上是犯了将一般当成特殊之错误。这本文学史是如此个性化,如此“专制”,让人印象深刻,它的“不全面”,恰恰反应出钱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信仰和坚持。这本书总会让我想到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一部私家的文学阅读史,因为在讲述过程中,他们都会偶尔跑题,生发出一己之感慨。记录它们的,将它们保留至今公诸于世的陈丹青和叶龙,同样是木心与钱穆的忠实弟子。他们在听课时就听到了老师内心的声音,明白了老师透过文学所要讲述的东西。钱穆三言两语的比喻,偶尔钻出书页,竟让人掩卷不忘。和木心五彩斑斓的光华用语不同,钱穆的比喻是平实的,像调味的盐,少量,然而重要,他说“孔子像一间百货商店”“《孟子》文章,近似陶渊明,阮籍的诗,近似《庄子》”,一饮一啄,勾起的是中国文学点滴的珍味。钱穆怀抱着保存国体的信念,偏安一隅却不愿流亡在外,要在一门门课中捡起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中国文学史里,这个精神就是对“人”的尊重,就是曾经的先辈面对同样的动荡之世,依然保持心怀天下的忧思与关怀,他们的精神气质,就贯通在今天的钱穆身上。所以当钱穆说出“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时,他是焦灼的,也是自信的,他相信自己的尝试能够接续中国文学的根脉,能够让中国古典文学的贵族精神在新亚书院的学生身上继续流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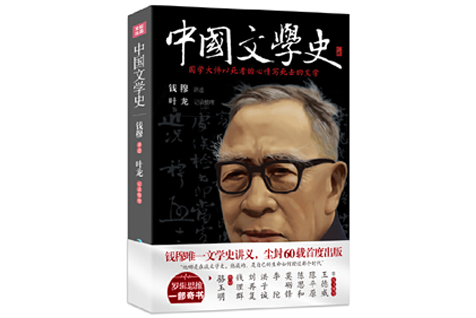
领书计划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