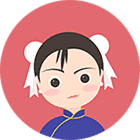领**
Lv.0
2022/08/19 08:49
第十六天
钱版《文学史》《经济史》的爆红,让叶老特别欣慰。他多次对我讲,自己这一生的成功,都和写字有关。他的子真的很漂亮,是那种簪花小楷,端端正正的,有金石之气。这样的笔迹,多半都是“童子功”。叶老出生于1928年,他说自己小时候每到暑假,总不能玩耍,因为父亲的严厉要求,他每天要练习整整六小时的毛笔书法。因为写字而改变命运,在叶老的一生中,发生过多次。而最具转折意义的,至少有两次。第一次是1947年。他刚从省立绍兴中学毕业,还不满20岁,没钱升大学,父亲又病故,只好写信给一位世伯,托世伯的女儿帮忙找工作。很幸运,这位姐姐的先生在南京国民政府工作,正需要请一位“书记”,叶老的一手好书法,当下就被看中。那一年他挥别母亲,去了大城市南京,自此一去不回。在南京国民政府,叶老受过专业、严格的速记训练,这给他后来的课堂笔记记录埋下了伏笔。1949年,政局大变,叶龙先是随国民政府机关转移到了广州,很快又接到迁徙重庆的命令。早就听闻蜀道难,叶龙不愿随迁,走到湖南的时候,就选择了脱离,在湖南武冈乡下的一间小学教书,教了半年多,等待全国解放。谁知,取得全国胜利后,叶龙的家乡又开始缉捕托洛茨基派。他的两个朋友因为信奉托洛茨基被捕,他因此受到牵连,没法回乡,只好转往浙江舟山,试着再谋生路。阴差阳错,他进了舟山的“蒋军官兵收容所”,又被遣回亲戚所在的籍贯:湖南沅陵。他千山万水,又回到湖南,这次在一家酱园做学徒,白天送货,晚上看门,一晃又是半年。他中学毕业就做了少尉书记,如今一辈子要做个小学徒,有什么意思?那时的叶龙刚满22岁,在信息闭塞的乡下,他听收音机、看最新的杂志、和笔友通信,心中充满了不甘,还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一份香港的左派报纸,给他带来了希望。有一天,叶龙在当地的新华书店看到香港《周末报》上刊载的文章,介绍香港调景岭难民营的情况,说救济粮每天吃几餐,还有奶粉、维他命,待遇很好。他心想,做难民这么好?不如到香港闯一闯。那是1950年。叶龙一路向南,经过广州,过了深圳,直到香港关口才停下脚步。他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当时,警察用粤语问了一句“你从哪里来?”他听得一头雾水,因此被拒入香港。原来,1840年以后,港英政府有规定,广东人可以自由出入香港,不是广东人就不行。幸运的是,叶龙在关口附近遇到“黄牛党”,花了点钱,到了晚上,“黄牛党”背着他过了深圳河,这才踏上香港的土地。关于那几年,叶老谈得并不多,而且语焉不详。我想,他身上一定有很多秘密。理解1949年,比我们想象中要困难得多。我还记得,第一次到叶老家做客的情形。临走的时候,他突然拉住我,说要唱一支歌给我听。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南京到北京,哪一个不文明?人民的领袖,就是那毛泽东。”这是一首红歌。解放初期在湖南沅陵的乡下,叶老停留大陆的最后一站,偶然从收音机李听到这首歌,就记了下来,一直记到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说“最爱的还是这首歌”。我很意外,也有很多的不理解。在我看来,叶老在1949这一年的故事,是无数小人物在那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政府小职员,因为政治的原因颠沛流离,几乎无路可走,又因为一首曲调欢喜的红歌,就莫名地消解掉颠沛命运的怨怼,爱上一个他基本没有经历过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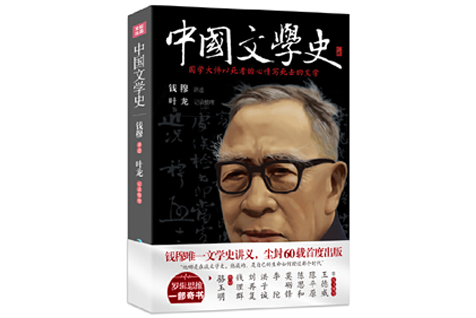
领书计划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