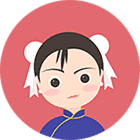领**
Lv.0
2022/08/21 17:41
第十八天
1989年,钱穆病逝前一年,回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在下榻的百乐酒店做了一场小范围讲学,论题是《天人合一观》。那天的听众,有钱穆在新亚的老同事、法学家罗梦册,有新亚最早的毕业生唐端正、梁思朴和刘若愚,还有钱穆去台湾以后与之过从甚密的何佑森、逯耀东,以及罗梦册教授带来的两三位研究生。叶老也在其中。这不是世人公认国学大师钱穆的最后一课,却是叶龙眼中的“最后一课”。那一年,他61岁,最后一次为恩师做授课记录。那篇文章题为《论天人合一:宾四先生的亲身领悟》,后来发表在台湾的一份报纸上,仅1296字,却被钱穆视为自己“晚年最后的成就”。前面讲到,因为写字而改变命运,在叶老的一生中,发生过多次。一次是1947年,另一次就是1953年。叶老进入新亚书院,很快就因为笔录快,而且准确,加上对浙江口音没有障碍,被指派专门替钱穆先生做演讲记录。其实很早,钱穆就在自己的著作里提到过叶龙。1970年,他那本著名的读史小册子《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台湾初版,钱穆特地补写了一篇序言,提到“这个讲演集,是由我一个学生叶龙记录,再由我整理润饰的。”(图片1)这张图片是1961年叶龙在孟氏基金会举办的学术讲演上,被委派为钱师讲演“中国历史研究法”作记录。钱门弟子何止三千,然而像叶老这样把发扬恩师学说当成自己一生志业的,恐怕数不出第二个。世人往往看重亲笔著述,轻视口耳相传。其实,在文字出现以前,远古时代的人类正是通过以口相授来传承历史的,所以有“十口相传为古”的说法。如果说孔子是古老的口传文化时代的最后一个圣人,《论语》是一部伟大的口传文化典籍,那么我们,同样不能以“著书立说”的单一标准,来判断钱穆旅居香港办学的16年。这16年,钱穆在著书立说方面几乎没有作为。可是在课堂上,他留下了数不清的思想火花。这其中,既有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有中国思想史的通俗演绎,更有成体系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如果没有门下弟子的原始记录和辛勤编纂,钱穆这一时期的思考成果将永远湮没于历史,而“钱学”的完整框架,也将永缺一角。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叶龙在历史中的坐标,也许才更加清晰。要知道,整个五六十年代,叶龙几乎是钱穆先生的御用记录人。只要有讲座,都由他随同记录。大量记录稿在整理、誊正以后,钱穆先生都极为仔细地作了修改,甚至在钱穆先生1967年去台湾以后,叶龙仍然不断地,把自己记录的“讲学粹语”寄给老师修改。在两个人持续多年的通信中,涉及讲稿整理的段落竟然多达半数以上。整理学者的讲稿,这种困难,比翻译他人的著作,有过之而无不及。要记录的完全正确已经很难,还要做到信、达、雅这三个标准,就难上加难了。叶老所做的工作,钱穆先生是否认可?我想,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他不但是认可的,而且有所依赖,否则也不会在信中说“盼细加寻索。此后若陆续写来,当为陆续改正。”(图片2)这是叶龙1955年使用的《中国文学史》笔记本。(图片3)这是叶龙保留的钱穆授课课程表。说到这里,还要补充一个细节,2014年,叶老还做了一件大事。他详细考证了钱穆先生1948年应上海正中书局的邀请,编选100本中国古籍必读书的前因后果,还原出了这份夭折于战火中的书单。这项重要的考据工程,在当年曾经引起很大的反响,给“钱学”研究做了补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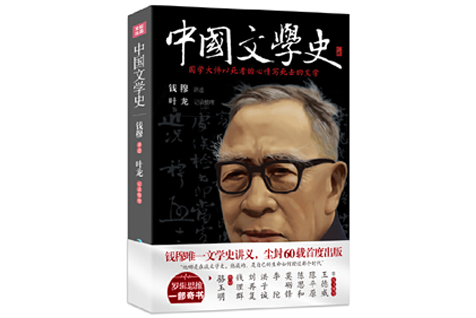
领书计划详情